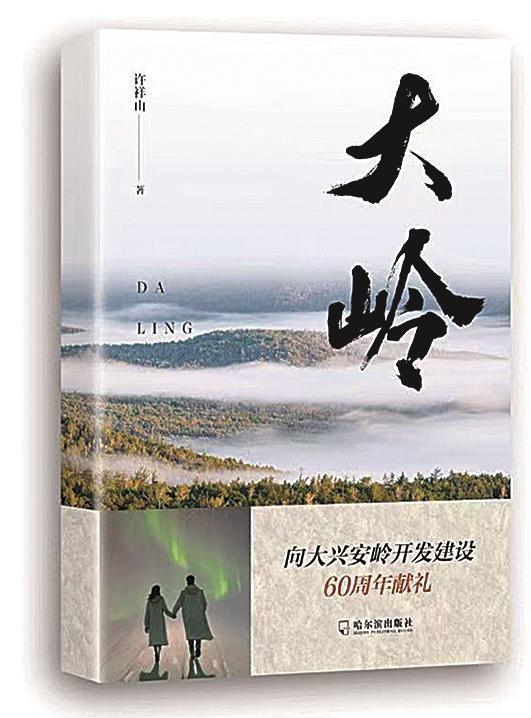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
《大岭》主要讲述的是一位在大兴安岭成长起来的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志气、有才能的青年企业家蒋兴面对大兴安岭资源危困的局面,毅然放弃到南方城市发展的机会,以年轻人的担当、锐气、果敢,直面企业逆境、挑战林业经济危局的故事。主人公蒋兴借大兴安岭进行二次创业、强区富民和产业结构调整之机,经过艰苦创业,锐意改革,开拓进取,把一个曾因经营不善,管理混乱,濒临倒闭的国有木材加工厂——兴北厂救活成为富有生机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新型企业。
倾情演绎大山深处创业者的时代之歌
——品评许祥山的长篇小说《大岭》
□张景臣
花了整整一周时间,心无旁骛地品读了许祥山的长篇小说《大岭》。在阅读碎片化和娱乐化的当下,能够静下心来品读一部长篇小说,除了读者有极大的耐心,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有吸引人读下去的理由。这一点,我在《大岭》里就深深地感受到了。读罢掩卷,回顾自己一周来阅读的心路历程,不由自主生出诸多感慨来。小说所讲述的创业故事、塑造的血肉丰盈的人物、令人双眼含泪的情节……叫人心绪久久不能平静,感动之余,也产生了对作家和作品的双重敬意。那么,《大岭》究竟“好”在哪呢?
独特的语言气质
小说贵在“说”字。这个“说”就是通过语言进行叙述,推动情节向前演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语言是第一重要的。它既是作家打开百宝箱的钥匙,也是作家发给读者的通行证,更是作家生产产品的“品相”。
阅读《大岭》这部小说,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作家语言运用的“老道”。这种“老道”既不是老气,也不是世故,而是作家洞察事物后的冷静和自信。这就使得这部小说的语言朴实无华、自然流淌、不加刻意雕琢和粉饰,却又张弛有度,耐人寻味,能够充分反映作家的文学修养、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。
特点之一:精炼与精准。精炼的语言能突破冗余的遮蔽,有效提高表达的效率和精准性,充分展现作家的语言把控能力。《大岭》在语言运用上,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和提炼,小说通篇采用短语、短句,并且有意识地减少修饰词的使用,使语言给人的感觉既干净又“干练”,有一种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艺术境界。比如,在介绍木材厂现状时,作家写道:“尽管这样,厂子仍然像扎了眼的气球——吹一下,鼓一下,最后还是瘪下去。”寥寥数语就把事情说清楚了,如果实写,恐怕就得弄出篇报告来。与短语、短句相匹配,小说在谋篇布局上也通篇采用小段落,充分照顾到了读者的阅读体验。
特点之二:意象与画面感。语言的意象是用文字调动读者的想象,使人通过多维感官在脑海中形成画面感。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可感性。纳博科夫说:“好的描写应该让读者用舌尖舔到文字的味道。”品读《大岭》的语言,给人强烈的感受是作家特别善于“造境”,他总是试图通过以字符营造出的意象和画面调动人的感官,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。比如,对白桦林场的描写:“十几座二三层小楼像几只引颈的松鹤恬静地站在广阔的雪原之中。”这是不是令人好像看到了一幅版画?文中这样的句子会时常冒出来,令人每每读到都眼前一亮。
特点之三:节奏与音乐性。米兰·昆德拉说:“语言是音符,句子是旋律,而小说是交响乐。”语言节奏与音乐性的融合,既是形式美学的追求,也是情感表达的载体。品读《大岭》,给人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作家的语感特别好,他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通过遣词和节奏让语言流动起来,使文字像跳动的音符具有了音乐的旋律。具体来说,就是语言的诗化。诗化的语言,能够反映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灵敏的感觉,更能增强作品的可读性。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小说中那些关于自然和景物的描写,虽然文字不多,但却诗意浓厚。当然,只要你细心品味,小说中诗化的语句随处可见,上边所列举的例子就同时兼具了这一特质。
特点之四:情感与哲思。小说语言不是装饰,而是思想的容器。米兰·昆德拉说:“好的小说语言像镜子,既映照现实,又折射心灵。”用语言传情达理,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难题,作家更是如此。优秀的小说往往通过隐喻、留白、通感等手法增强语言的张力,在情感共鸣和哲学思辨中架起桥梁,让人读罢啧啧赞叹。品读《大岭》,通篇没有一句说教的言语,作家以其深厚的文学底蕴,把他的思想融入艺术性的表达之中,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。比如,他写下海经商:“看人家先下海的摸着鱼了,有的摸的还是大鱼,可等你下去了,或许连虾米也捞不到,反而被呛了几口水。”这样的例子在文中不胜枚举。
立体的人物精神向度
一篇好的小说,除了语言,第二重要的就是人物塑造。人物不可老生常谈、似曾相识,要鲜活生动,有立体感。《大岭》中出现多个人物,作家在塑造他们时,既倾注了足够的热情,又极尽想象之能事,哪怕是很“小”的人物,都努力避免扁平化,成功地为读者呈现了一组立体生动的人物群像。
其一,人物刻画。一般来说,刻画人物主要围绕生理、社会、心理三个维度来进行。生理维度主要是对人物外貌体征的描写,最有代表性的是女主人公叶兰。叶兰是个美女。给人的感觉是,作家在设计这个人物时,就先于男主人公“爱”上了她。所以,作家对叶兰的形象描写也贯穿始终,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场合、不同情境下都不惜笔墨,倾情赞美,让读者也情不自禁地“爱”上了她。
社会维度主要是指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,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男主人公蒋兴,因为《大岭》所讲述的实际上就是一部蒋兴的创业史。作家在刻画这个人物时,也着重让他在社会关系中“立”起来。通过书写他创办兴北野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、岭北木业集团公司的经历,成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正直、刚毅、果敢、富有开拓精神的人物形象。
心理维度主要是指人物的潜意识和精神世界。写“心灵”对每个作家都是个难题,但又不可回避。因为人是有思想的,只有揭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,才能使人物鲜活起来。作家当然深谙此道,所以在塑造蒋兴这个人物时,围绕夫妻关系、婚姻家庭以及和叶兰的情感纠结,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描写,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蒋兴情感丰富复杂的另一面。
其二,动态演变。罗伯特·麦基说:“如果你的主角在故事结尾毫无改变,你写的只是流水账。”小说人物塑造是个动态的过程,需要随着叙述的推进逐步呈现出多元性。《大岭》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。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,既展示了外在表象,又“安排”了人物多舛的命运。于是,我们看到,蒋兴在创业成功后得了胃癌,玉茹也因此放弃了离婚的念头;叶兰终于找到父亲后,父亲却因车祸死亡;老铁道兵陈向阳因为发挥“余热”,被几个窃贼气死;维维因为婚姻不幸,堕落于滚滚红尘中等等。这些人物的结局既让人感到惋惜,又足以震撼人的心灵。不是作家残忍,生活现实映照艺术现实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。恰如古希腊一位哲人所说:“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。”
其三,功能人物。小说创作是一个破茧抽丝的过程,作家在写作中为自己设置了很多难题,有些难题无法破解,就需要功能性人物登场了。《大岭》典型的功能性人物有两个,一个是警察爱军,另一个是酒吧小姐维维。爱军是蒋兴的妻弟——小舅子,他深深地爱着叶兰,叶兰也真心地喜欢他,并且最终走到了一起,使蒋兴不得不发出“幸亏自己没有失去理智”的慨叹。可以说,在这部小说中,他是最大的“赢家”,他不仅得到了漂亮的叶兰,还成功帮助蒋兴实现了自我救赎,也让作家成功跳出了“男人有钱就变坏”的世俗窠臼。而维维呢,虽然是个负面人物,但作家在塑造她时却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,不但没有任何的贬低,还写出了她很多可贵的品质。正是因为她的呵护,才使得叶兰虽然也在酒吧打工,却实现了出淤泥而不染,否则,后面的所有故事就都不会发生。可见,功能性人物有多么重要。
双轨制的情节推动
情节较之语言和人物分量轻些,但又是相辅相成、离开它不行的一个重要机制。小说情节是展现故事发展和人物关系的重要手段。小说情节的推动是故事发展的核心,它通过一系列事件和冲突引导读者深入情节,保持阅读兴趣。《大岭》在情节处理上,采用的是双轨制并行的运行机制,主线是蒋兴创办企业,副线是叶兰寻找父亲。围绕这两条线索,作家采取多种“措施”吸引读者进入故事——
制造矛盾冲突。冲突是情节的核心,无论是人物间的矛盾、内心的挣扎,还是与环境的对抗,都能推动故事发展。《大岭》中有许多矛盾冲突。这不难想象,干事创业哪能像吃饺子,遭遇难缠的人和事是家常便饭。比如,蒋兴处理工人闹事,处分违纪员工,解决销售难题,与外商较量以及处理与妻子玉茹和叶兰的情感纠葛等等。有的难题“当场”解决,让人拍手称快;有的难题直到最后才给出答案,读罢让人恍然大悟。
展现人物动机。人物的目的和动机是情节发展的驱动力,他们的选择与行为直接影响故事的走向。《大岭》在展现人物动机方面交代得很明确。蒋兴的动机就是面对资源危机、经济危困要闯出一条新路来,叶兰的动机是寻找亲生父亲,玉茹的动机是经商做买卖,爱军的动机是娶叶兰当老婆,维维的动机是挣足了钱回去找个人嫁了……正是不同人不同的动机,推动了事物的向前发展,也丰富了小说的内涵。
设置转折点。转折点是情节中的关键时刻,通常会带来重大变化,推动故事进入新阶段。《大岭》中作家精心设置了多个转折点,都为情节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比如,蒋兴要账偶遇对方企业的老板娘,企业打不开局面启用新的销售员,蒋兴和叶兰遭遇车祸和绑架,叶兰在寻父线索中断时收到宋志成想起的叶文峰老家的地址等等。这些,都为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局面。
有意控制节奏。情节的节奏既要有紧张的高潮,也要有缓和的过渡,以缓解读者的阅读疲劳。这应该属于写作的技巧范畴。在《大岭》中,作家对主线的推进主要是通过使用闲笔、留白和心理描写、节外生枝等手段来进行控制的。而对于副线的推进,作家一开始就没想让叶兰和读者很快找到父亲,所以,在用笔用墨上便一点也不着急。因为从阅读的角度来讲,副线其实对读者更有吸引力。对此,作家心知肚明,便耍了这个小“伎俩”。但也正是这个“伎俩”,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,又突出了主题主线。
打磨人物对话。对话兼具推动情节、揭示人物、取悦读者三项功效。好的对话能够三言两语就刻画一个人物——比如书记王富楼的形象,能够把作家想做的“事情”通过人物先介绍出来,节省许多需要过渡的“口舌”。但是,所有的作家又都“惧怕”对话,因为对话一旦写“磨叽”了,不但不能有效地推动情节,反而还会起副作用。令人欣喜的是,《大岭》中所有的对话作家都进行了精心的雕琢和打磨,其中有许多神来之笔,不得不令人赞叹。比如,写陈向阳和老战友宋志成在病榻前相见的那一幕,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问候,但在那个情境下,却饱含了两个老人无限的深情,叫人不禁潸然泪下。
多元的现实意义
小说不仅是虚构的艺术形式,更是折射现实、干预社会、重塑人性的重要载体。文学作品的功能是教化而非教育,这种“化”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实现的,其意义往往蕴含在题材中。
《大岭》所讲述的故事,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林区进入资源危机、经济危困的“两危”时期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以蒋兴为代表的一众林区人,他们先知先觉,为节约资源、打破“独木支撑”的经济格局,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。尽管故事的发生不是现在,但对今天的我们,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,正如美国作家辛格所说:“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,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。”
第一,传承弘扬精神文化。大兴安岭开展建设60年,靠的是一代代林区人的接续奋斗,靠的就是以“突破高寒禁区”为核心的大兴安岭精神所激发的奋进力量。《大岭》中的人物正是这一精神形成的核心要素,也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和弘扬者。如今,“林一代”大都已长眠于白山黑水之间,“林二代”也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,一大批年轻人已成为时代的主角。新的历史条件下,如何传承弘扬好大兴安岭精神,激励新一代的建设者传递好历史的接力棒,对于实现林区转型振兴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。鲁迅先生说:“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,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。”从这个意义说,《大岭》有着积极的作用。
第二,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。随着2014年全面停止木材商业性采伐,大兴安岭彻底断绝了对“大木头”的依赖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,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,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,我区大力发展生态主导型产业,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,努力打通“两山”转换通道,在这一进程中,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会更加严峻,这就不仅需要继承发扬好大兴安岭精神,更需要新时代的建设者们进一步解放思想、挺膺担当。“所有写作都是政治行为,逃避现实的文学不过是劣质浪漫主义。”许祥山无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,他作为林区的建设者之一,以敏锐的洞察力关注到了这一点,并以文学的形式倾情演绎了大山深处创业者的感人故事。尽管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,但故事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和创业精神,以及他们所进行的积极有益的探索,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第三,文学创作的典范作用。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,60年来,大兴安岭的文学创作也成绩斐然,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。但随着网络和AI时代的到来,我区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人员老化、后备力量不足、群体效应不明显等问题。《大岭》的出版发行,从写作角度,必将引起我区作家的高度重视和深度思考,也必将激励更多文学爱好者,坚守写作初心,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绽放异彩。
当然,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是因人而异的,一个人的观点难免局限。小说的现实意义,笼统地说,正在于它既是时代的镜子,也是照向未来的探照灯。
期望,有更多的读者能够认真读一读这部小说。
 黑公网安备23272202000048号
黑公网安备23272202000048号